
俯瞰禹王峽。
青海新聞網·江源新聞客戶端訊 許多年后,當馬進才面對這片親手種出的、已能蔽日遮天的綠蔭時,準會想起很多年前,和父親在自家自留地邊栽種楊樹的那個遙遠的早晨。
那時禹王峽兩岸是白的——不是雪白,是正午毒日頭把滿坡碎石曬出的那種枯燥的蒼白。
褲腳沾著草屑,鞋縫嵌著泥土,馬進才的目光撫過眼前的每一棵樹,眼神柔軟似水。這片他守了31年的土地,是黃河流經青海的最后一道峽口,名叫禹王峽,也叫寺溝峽。
若是你問他,這些年共種了多少棵樹?他黝黑的臉上會浮現出溫和的茫然:“沒數過,也數不清。”花了多大力氣?他憨厚地笑笑:“一天不來看看,心里就空落落的。”樹都種在哪兒?這個他答得上來:“崖頭上,陡坡里,坑坑中,黃河邊邊……越種越遠,越種越密。”
我們是在一個秋日上午見面的。同為土族,當我用母語問候時,老人先是一愣,隨即笑開了滿臉皺紋,像忽然卸下了一層無形的殼。
“我阿爸(父親)馬子西龍,就愛種樹。”馬進才說。在他小時候,父親就常帶他在房前屋后栽樹,一邊培土一邊念叨:“前人栽樹、后人乘涼。”父親的手很大,很粗糙,覆在他小小的手背上,一起把樹苗扶正。那種觸感,混合著泥土的腥氣和樹皮的清香,穿越幾十年的歲月,依然清晰。
或許,那顆綠色的種子,早在那時就已埋下。
只是,父親種的是家宅旁的蔭涼,而馬進才想種的,是整個禹王峽的春天。
1994年春天,45歲的馬進才從自家院里挖了一棵山杏苗,扛起鐵鍬,上了山。沒有路,碎石硌腳;沒有水,得繞行去黃河邊挑。第一趟下來,扁擔把肩膀壓出深紅的印子。
來年春天,那棵孤獨的山杏,顫巍巍地頂出幾朵粉白色的花苞。就是這點微不足道的粉色,像一簇火苗。1995年,他辭去村黨支部書記的職務,專心種樹。
“辭職,種樹?”村里人覺得他“犯神經。”老伴問:“圖個啥呀?”他沉默半晌:“我要讓寺溝峽綠起來。”
幾天后,馬進才背著8棵指頭粗細的樹苗,再次上山。一桶水20公斤,只能澆四棵樹。8個“孩子”,至少需要他在這條亂石坡上往返兩個來回。日復一日,這條取水路被他踩出了模糊的痕跡。
8棵樹全活了。1996年春天,馬進才又找來十幾棵樹苗。“等到60歲,我要種活60棵!”從此,春天栽苗,夏天抗旱,秋天修枝,冬天防寒。荒坡每多一分綠意,他腳下的步子就輕快一分。
樹越種越多,馬進才看到誰家院里有合適的苗子,便軟磨硬泡討來。樹越多,水的需求越大,有時一天要在黃河崖頭間往返10趟。冬天,怕羊啃樹皮,他用紅土拌成泥,一棵一棵用泥土包裹起來,像給樹穿上冬衣。雨天路滑,他曾幾次腳下一空,身子在崖邊晃蕩。回到家,只對老伴嘿嘿一笑:“沒事,擦破點皮。”
2005年,看見幾個孩子在扒一棵榆樹的皮,那樹已露出近一米長鮮嫩的樹干。馬進才急得聲音發顫:“這樹皮跟人的皮肉一樣啊!剝了,它就活不成了!”他把孩子們領下山,挨家挨戶去說,情急時,也難免用柳條嚇唬淘氣的孩子。鄉親們感嘆:“這老馬,把樹當成娃了。”
歲月像黃河水一樣流走。到了2012年,馬進才已在這山上獨自耕耘18年。親手種下的樹已有數千棵,加上自然生發的,大大小小上萬棵樹苗,終于讓綠意爬滿了懸崖峭壁。禹王峽的春天,被他一點一點,親手“種”了出來。

馬進才背樹上山(受訪者供圖)。
2013年,禹王峽景區建設啟動,機械開進了山。這時,所有人都覺得,老馬該功成身退了。在西安的小兒子一次次打來電話:“阿爸,回來享享福吧。”65歲的馬進才,坐在那棵最早的山杏樹下,想了很久。山風穿過枝葉,鳥鳴清脆。他搖了搖頭。根,已經扎在這里了,拔不動了。
2014年,馬進才成了禹王峽景區的一名管護員。不用再背樹苗,但他依然每天清晨上山。游客多了,他又成了義務講解員,用那口質樸的鄉音,講大禹的傳說,講黃河的故事,講每一棵樹的來歷。說起這些,他眼中光彩流動,如數家珍。
今年,馬進才被授予青海省道德模范。在西寧的勝利賓館,他站在明亮的燈光下,胸前戴著大紅花。當被問及站在會場接受表彰是什么感受時,他半天沒作聲,有些靦腆地笑了笑,說出的話卻讓人一愣:“開會那棟樓后頭,有個小花園。我看見里頭長著竹子,青翠翠的。青海這地方,竹子可不多見……等開了春,我想法子移一棵小的,帶回禹王峽試試。”
和馬進才老人一道走在禹王峽景區的小路上,他對著蒼茫的黃河與群山,哼起了“花兒”:“大禹治水著到三川,腳印哈留給了人間……”歌聲粗糲卻深情。
后來,當地村民在這歌謠后面,加上了兩句新詞:“老馬種樹的禹王峽,游客們浪哈的干散!”
馬進才,沒有傳奇。他只是用一生,把父親在他童年時種下的那顆關于“綠”的種子,細心呵護,然后讓它在這片古老的山峽里,開出了一整個春天。
(攝影:除署名外均為本報記者 張多鈞 才貢加 潘昊 楊紅霞 實習記者 張富昭)
(來源:青海日報)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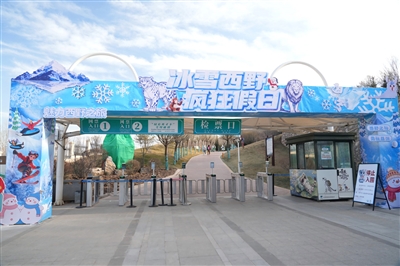











})
})
})
})